01
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(以下简称《哪吒2》)能获得惊人票房,并非偶然。
我此前说过,受到观众欢迎的电影,一定要在某种程度回应社会焦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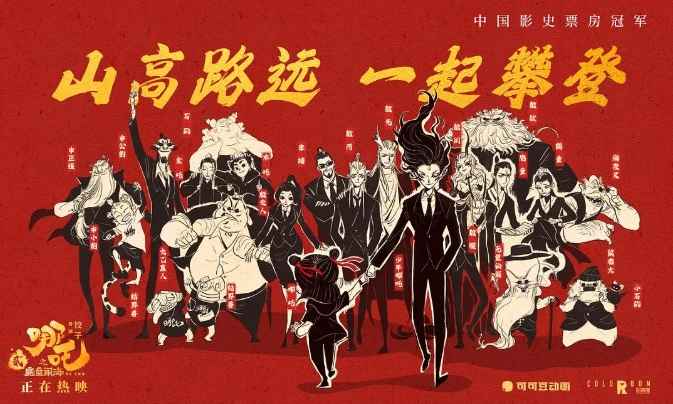
《哪吒2》讲述了一个“受骗-觉醒-复仇”的故事,这触动了今天几乎所有国人心底的一道隐秘伤口——一个人没有受骗的经历,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但在现实生活中,大多数人只能止步于“受骗-觉醒”,向骗子索偿并复仇是遥不可的,并可能会带来极大麻烦。
而在影片中,哪吒不仅砸碎了骗子的主要道具“天元鼎”,而且把首席骗子“无量仙翁”打得鼻青脸肿,落荒而逃,这是何等解气?

自八十年代以来,中国一心想“融入”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,却不断受到美国霸凌,大多数情况下,中国采取了“吃亏是福”、“能忍自安”的态度,这成了许多国人的心中块垒。
导演饺子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观众的这一心理,所以在影片中设置了许多隐喻。
比如,做为诈骗与邪恶的中心,玉虚宫“很白”,哪吒步入其中时,一直在说“好白,好白”,就差直接说“白宫”了;做为诈骗与特权的主要象征物,无量仙翁派发的有美国鹰logo的绿色玉佩,则暗喻了曾令无数国人心往神驰的“绿卡”;做为主要犯罪工具的天元鼎,上面则赫然镌刻着美元标示……

到了哪吒与无量仙翁决斗的高潮,哪吒喊出了“你们自诩照世明灯,干的却是恃强凌弱,祸乱人间的勾当!”这是在直斥谁,已经不言而喻了。
其实,在我看来,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,何必再生造“照世明灯”这样的新词?倒显得有点遮遮掩掩,直接说“文明灯塔”,岂不更爽?
影片对不可一世的美国如此“含沙射影”,自然会令“忍你很久了”的观众会心一笑,并且产生了“我知道你在说谁,但我不说”这样的特殊快感。
影片这样设置“暗桩”,表明像饺子这样的年轻电影人,正在经历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,他们令“第五代”渐渐显影为某种辛亥之后仍然拖着辫子的形象。
在一个早已原子化的世界里,人们唯一可欲并且可得的庇护与依靠,就是亲情。饺子显然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,努力将亲情打造成影片的主要支点与泪点,获得了极大成功。
但也必须指出的是,影片对父亲情深,渲染太过,有点透支了。在一部电影里,居然安排了三组雷同的亲情关系——哪吒与父母,敖光、敖丙父子,申公豹与父亲和弟弟。
这三组人物都相亲相爱、在天罗地网中努力打拼,屡屡碰得头破血流,时时经历生离死别,甚至连彩蛋里都还有申公豹和他爸爸。

似曾相识的套路,加了太多味精的鸡汤,一次又一次地端到观众嘴边……一个大IP拿来这样搞,这不是自我降级,暴露自己的思想贫困吗?
更大的裂隙还在于:哪吒本是“剔骨还父,削肉还母”的人物,宁死也要摆脱父权的束缚,但在这部电影里,却和父亲李靖以父慈子孝的形象出现,构成中国传统语境中理想的父子关系。
可是,孝顺的魔,还是魔吗?当哪吒狂傲地宣布,“小爷是魔,那又如何”时,他究竟在说什么?

《哪吒2》的票房如此之高,还因为饺子导演显然深谙商业片的票房密码——用密集的笑点取悦观众。
遗憾的是,本片的搞笑桥段大多停留在肢体搞笑与网络烂梗的拼贴上:方言谐音梗、刻意扮丑的配角设计等等,令影片的喜剧感显得廉价且过时。

其实,《哪吒1》就有这样的问题,很多桥段相当低俗,但就是不改,可能导演觉得越低俗看的人就越多吧?在《哪吒2》中,踩仙女的裙子、向饮料里撒尿,做藕粉时抠脚、擤鼻涕、猪放屁、吃呕吐物……全然不顾本片预设的观众主要还是小朋友。






